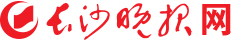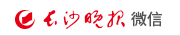报告文学丨霹雳一声

范亚湘
遇险
1927年9月9日拂晓,铁路工人相继破坏了粤汉铁路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南下和北上的火车都到不了长沙,阻断了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向长沙调度。
酝酿已久的秋收起义揭开了序幕!
这天中午,几位身穿白色褂子和灯笼长裤、打扮成安源煤矿采购员的人风尘仆仆地走在从江西安源到江西铜鼓的路上。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央特派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和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一行人,他们急着赶到铜鼓,就是要靠前指挥铜鼓的革命武装,“霹雳一声暴动”。
此前,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湖北、湖南各地的路上都增设了不少反动民团的哨卡,肆意捕杀“赤化嫌疑犯”。
当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张家湾时,忽然从路旁的树林里窜出几个端枪的反动民团:“站住!”阳光下,枪上的刺刀白晃晃的,直指毛泽东和潘心源:“干什么的?说!”
毛泽东不慌不忙,掏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安源煤矿介绍信。反动民团领头的是一斜挎着“王八盒子”的副官,他接过介绍信乜了一眼,打量了一阵气度不凡的毛泽东和潘心源,陡地收起介绍信,厉声吩咐手下:“带回总部去审讯!”
几个团丁将毛泽东、潘心源等人用绳子绑着手,用枪押着。毛泽东等佯装听从团丁的指挥,磨磨蹭蹭地走在去反动民团总部的路上。
走了一段,毛泽东向潘心源使了一个眼色,潘心源心领神会故意趔趄了一下,刚好踩在毛泽东的鞋帮上。“走路长眼睛啊!”毛泽东责怪了一句,借机站住,等待一名团丁帮他提鞋帮。潘心源和其他几位却没有停留,反而加快脚步朝前走了。副官见状,大呼大叫去追潘心源,剩下两个团丁押着掉在队伍后面的毛泽东。
火火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枝头上的知了像是着了魔似地叫个不停。毛泽东知道,其实团丁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吃上一口饭而加入地方反动武装。
潘心源几人越走越快,已把毛泽东甩了一大截。走到一个拐弯处,毛泽东边走边故意将衣服口袋里的大洋弄得哗哗作响。大洋一响,两个团丁眼泛绿光,端枪的手都没力了。见此,毛泽东放慢脚步,笑着对两位团丁套近乎:“两位老总如果急需用钱,就别客气!”
两个团丁各自吞着口水,伸手去毛泽东衣服口袋里掏钱。“慢着!”毛泽东一笑:“就怕两位老总不肯放我一马啊!”
两个团丁互相看了一眼,又张望了一下前面,押着潘心源等的副官已没了身影。一个团丁小声对毛泽东说:“转个弯,就到总部了!你把钱给我们,快点跑吧!”
两个团丁各自抓了一把大洋,藏好。然后,他们毛手毛脚地给毛泽东松了绑,示意毛泽东朝另外一个方向快跑。刚等毛泽东钻进树林里,“砰——砰——”响了两枪,“有人跑了啊!有人跑了啊!”“砰——砰——砰——”两个团丁装模作样又放了几枪。
听到枪响,副官急折跑了回来。见状,潘心源几位立即相互解开绳索,迅速地消失在树林里。
副官一边骂着两个团丁,一边举枪搜索。夕阳西下,知了叫得更欢了,毛泽东早已跑出了追兵的视野。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毛泽东一生为中国革命历尽艰险,他有许多传奇经历,多次都跟死神擦肩而过。神奇的是,足智多谋的毛泽东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痕。
远的不说,“八七会议”前夕,毛泽东在武昌就上演了一出给前来抓捕他的特务“指认毛泽东”的“好戏”。
这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长江边。当毛泽东回走到六渡桥时,迎面遇上了两个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 ”
毛泽东心头一紧,但立马镇定下来。毛泽东从对方的问话中判断出这两个特务并没有认出他,便满脸疑惑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个子很高,像个教书先生,他就是毛润之。”两个特务比划着问。
毛泽东自然地用手往码头方向一指:“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朝着码头方向跑步追去。
毛泽东很快消失在街头,回到租住的武昌督府堤41号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云淡风轻地谈到了浏阳的这次被捕:“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200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天黑了,毛泽东光着划伤的脚,借着星光摸索着朝一户亮灯的人家走去。这是一户药农家,友善的药农接待了毛泽东。次日早餐后,药农先是帮毛泽东去临近集镇买了一双鞋和一把伞,还有几个浏阳茴饼,然后领着毛泽东抄近路向铜鼓出发。联络上铜鼓党组织和革命武装时,毛泽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个铜板,毛泽东风趣地将之称为“穷得叮当响”。

《秋收起义》油画 何孔德、高泉、冀晓秋、陈玉先
易帜
让时间倒回到1927年8月。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刚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准备把秋收起义放在湘赣边界,而是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他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湖南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力量,“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以上的把握”。
为了保证湖南秋收起义计划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任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为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并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先是小范围地秘密做了一番调查,然后就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
其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城,司门口的城门上悬挂着共产党人血淋淋的头颅。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和盘查,毛泽东将谋划秋收起义的会议开到了长沙北门外(今开福区潘家坪附近)的沈家大屋。
今天的潘家坪,已是长沙城北的繁华闹市。90多年前,这里还比较偏僻,四野都是菜地和荒山。沈家大屋是中共湖南省委设在此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据曾参会的长沙县农民协会特派员余西迈回忆,毛泽东等中共湖南省委成员常常身着长袍马褂,乔装成“小开”(“富家公子”之方言)到沈家大屋搓麻将、喝茶、聊天。
8月16日至18日,中共湖南省委前后在“沈家大屋会议”召开了两次会议。这几天,毛泽东、易礼容等提着鸟笼,摇着折扇会聚到此,看似品茗闲谈间,一次惊天动地的农民暴动计划日臻完善。
这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国民党左派”旗子,中共党内还有人对国民党存在幻想。就在沈家大屋里,这天,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动情地说:“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
讲到这里,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会后,毛泽东向中央特地写信解释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纵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就会发现,无论何时何地,他最注重的一条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这与毛泽东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公元976年,岳麓书院正式建立。1917年,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制匾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从湘潭来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其时每天从他的寓所推开窗,就能看到讲堂檐前高悬的那块“实事求是”匾额。
“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日后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作过精辟概括:“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积极去研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才能成功。
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彼时,由于国民党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事实上与长沙已经隔绝。毛泽东认为暴动力量不足,主张缩小暴动的范围,只在湘中四围各县举行暴动。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当即引发争论,有人说:“润之啊,咱们大家讨论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指示相左啊,在暴动计划上中央对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怎么能擅自改变中央决定呢?”面对质疑,毛泽东坦陈:“我们搞暴动必须从实际形势出发,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执行,但不能完全不顾客观条件地盲从,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通过多次争论,中共湖南省委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着手准备以长沙为中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随即,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新的暴动计划,认为起义“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不想,这一观点却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认可,8月23日,中央就此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等,并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等处暴动。
中央来信传达后,中共湖南省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还能不能坚持新的暴动计划?据彭公达回忆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面对不理解和压力,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开始了游说:“我们还是按省委的新暴动计划执行,我来向中央回信解释。”随后,毛泽东再次回信中央,据理力争,再三阐述理由:“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之所以“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因为毛泽东的一再坚持,秋收起义最终决定以长沙为中心发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绝,贸然举行全省暴动,必将招致巨大损失。可以这样说,在湘鄂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正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精神的真实写照。
暴动
秋收起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毛泽东决定先送妻子杨开慧回老家板仓。杨家保姆陈玉英多年后回忆:“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
不想,这次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分别成为永诀。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最后分别的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具体日期一直众说纷纭。8月31日,毛泽东听从杨开慧的建议,化妆成郎中从长沙乘火车到了安源。
9月初,毛泽东在张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和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人。会上,当毛泽东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即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时,当即决定联合驻修水的卢德铭共同起义。
安源布置妥当后,毛泽东一方面给修水、铜鼓等地革命武装去信,要求共同举事,一方面自己亲自赶往铜鼓,欲与当地的革命武装面商起义事宜,进而,发生了前文所述的那次历险。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这份命令同时还任命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和各团团长等。
9月11日,秋收起义枪声响起。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农民军,湖北崇阳、通城部分农民军和安源工人武装等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起义军的枪声分别在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响起。
很快,起义军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湖南境内的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
这天,毛泽东跟随铜鼓的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向湖南进发。
早在1911年10月,还在湘乡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投奔湖南新军。毛泽东用“毛润之”的名字入伍,在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师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毛泽东所在的湖南新军接到命令,就地解散,尚未过足军人瘾的毛泽东只好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自从1925年春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后,人们就被他的豪放诗情和磅礴气度所折服,因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以前从未打过仗的毛泽东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哪怕革命正处在异常艰苦的关头,他照样豪气干云,激情满怀!
秋收起义的烈火已经点燃,这自然也燃起了毛泽东的冲天诗情,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呼之即出:“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十分通俗地写出秋收起义军的名称和旗帜,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起义军声势浩荡的场面;“不停留”传神地写出了军情紧急,士气激昂,兵贵神速,力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暴动。一个“直”字体现了工农革命军坚决的态度,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重重”,反映工农遭压迫之深;“个个”,强调工农必然起来反抗压迫;“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写出了起义的时间和声势,犹如那黑密的阴云,饱含雨滴,就要产生巨大的雷鸣,这就是暴风雨的前奏曲,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形成燎原之势。
短短50字诗篇,将秋收起义描绘得晓畅传神,直抵人心。90多年后,人们将《西江月·秋收起义》醒目地刻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陈列馆玻璃幕墙上,硝烟虽早已散去,然而,还能从这首词中品出起义军当年的英勇无畏,感受秋收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心境时曾说:大革命失败前后,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豁然开朗。

电影《秋收起义》剧照。
转兵
来火枪、红缨枪、大刀长矛、猪屎炮……而今,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陈列馆的陈列,每一件都经历过炮火的淬炼,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会师操场、文家市大捷的战斗遗址、杨勇将军故居、积谷仓、河口大屋革命漫画、刘家祠堂标语、铁炉冲毛泽东栽种的板栗树,都在诉说一段段红色记忆。
秋收起义爆发后,由于强敌反扑,三路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部队从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而且,起义军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所到之地的“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起义军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还是从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改变原有的攻击长沙部署,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以图谋下步行动方针。
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准确判断,认为敌我力量差距太大,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不可能撼动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重兵把守的长沙,相反,工农革命军最终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三团会师文家市,前委和师部驻扎在里仁学校。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果断否定了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保存和蓄积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由于再次与中央的意见相左,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前敌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议决退往湘南”。
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毛泽东指着一张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其中段地势险要,峭壁耸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声势可以直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具有较大的战略优势与政治意义。
退驻井冈山,毛泽东胸有成竹。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500余官兵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整齐列队。毛泽东站在台阶上,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聆听毛泽东演讲不仅仅有起义军,还有附近的农民和几个爬在墙头的天真烂漫的小孩。没出几年,其中的两个小孩胡耀邦、杨勇成为“红小鬼”,后来,他们一人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一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
9月25日,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途中,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打下了江西莲花县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特派宋任穷送信给毛泽东,告知井冈山有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议起义军速去那里落脚。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之信心。
起义军经过短暂的修整后,继续南向永新方向前进。可是,部队自转兵南下以来,一路上连续作战,战斗力大大减弱,少数伤病员由于缺医少药而牺牲,害怕艰苦的余洒度等人不辞而别。
毛泽东为此内心焦灼,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马上解决这些问题,部队就很难继续前进。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针对少数人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说:“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去打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有成功。”
10月22日,毛泽东率领部队继续艰难地向井冈山转移。曙光已经出现,巍巍井冈已在眼前。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行程1000多里,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领导下,终将镰刀斧头红旗插在了井冈山上……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