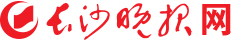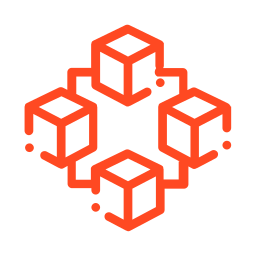湘江边的护路人
龚奕天
我的太爷,是湘江边的一个普通渔民。关于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外婆。
在夏夜的凉席上,冬日的火灶边,外婆把那些遥远的片段,一点点拼凑给我。于是这个只在回乡拜年时见过,已有些意识不清的老人,便在我的生命里有了模糊却温热的轮廓。
外婆说,太爷一生寡言,像江上沉闷厚重的浓雾。在战争与饥饿交织的年代,生活的网比太爷背上的包袱更沉,将他压成一道沉默、佝偻的剪影。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在饥荒的年月里,没让一个孩子饿死。外婆兄妹几人,便是他沉默的丰碑。外婆回忆时,苍老的声音会变得轻柔、迟缓。仿佛将我送回那个伫立于江边的老屋。“那时你爷天不亮就下江,捞到指头长的鱼仔都舍不得吃。晌午回来,蹲到灶边,把鱼刺剔得干干净净,鱼肉末全和在溜清的野菜糊里,分给我们几个细伢子。他自己呢,就端起碗,把沉底的野菜渣子喝得呼呼响。
太爷走后,外婆那双浑浊的眼眸噙满泪水,向我娓娓道来太爷与小道的往事。那是江边一条满是碎石的土路。外婆总记得太爷收工回来的样子:担子卸了人却还弓着,脚步缓慢。走着走着,便停下来,用那双磨得发白的布鞋尖,把硌脚的碎石子,一块一块踢到路边的草丛里。旁人问他“做么子踢石头子咯?”太爷头也不抬,只念叨着一句长沙土话:“做好事。”这在长沙话里,其实是“帮倒忙”“多此一举”之类的趣话。旁人听毕常常发笑,他也不恼咧嘴嘿嘿地笑,脸上的褶皱像被海水侵蚀的沟壑,透着一股坚毅。
踢石子的动作一直持续到太爷再也迈不开步,也深深烙印在外婆的童年记忆。现在外婆看见路上凸起的石子,脚尖都会不自觉地踢开,想着让后面的路人能走得顺当些,也替太爷走那条未完成的路。这个小小的动作凝结着江边讨生活的劳动人民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他们最懂得风浪的无常和个体的渺小。作为长辈,他们或许无力抵挡挨冻受饿,无力为子女铺就坦途,更无力对抗时代洪流,但他们可以一次次弯下佝偻的脊背,为后来者——也许是奔跑的孩子,也许是微胖的妇人,也许是眼花的老人踢开眼前这块梆硬硌脚的石头。这个笨拙的动作,包裹着他最温柔的善意。
如今,那条路已不复存在。但每当我感到前路坎坷,踉跄恍惚时,我总会想起他——我的太爷,他用一生的行走向我诉说:“真正的坚守,未必是开疆辟土,也许只是俯身清理脚下的一尺一寸。”太爷为我,为我们,在血脉里铺就了一条看不见的清幽小径——路旁没有碎石,唯有他那份沉默含笑的付出与坚守。
(作者系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初二7班)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