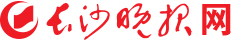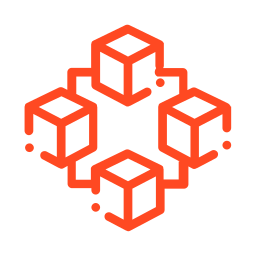童铃声声
杨松林
外婆家在一个叫水碧冲的山坳里,我记忆极深的小山村。
土砖屋依山而建,矮矮的,散落在弯头旮旯。偶见几户白墙黛瓦,很是打眼,外婆家便是。
山冲人家有赶早的习惯,赶集、放牛、进山砍柴……就连挖土、栽菜都不例外。外婆起早做饭,外公、舅舅从田间、山头扛着锄头,挑着箢箕,扦担杈满柴,回来了,围着大桌子吃早饭。那是红薯丝、南瓜汤当饭的年代,白米饭精贵,外婆总要在我的洋瓷碗里多装点。
乡下人说的打点,就是打铃。外婆尤其注意。她吃饭时,旁边一定会放闹钟。八点尚差一刻,她就急急地催我去打点,还特地嘱咐要打得响亮些,好提醒社员们得出工哒。
打点的地方在屋后山坡的一棵大树下,平日里,外婆就把我带到那儿。野草蔓蔓,荆棘遍地。我在前边走,她在后面护着我。到了,外婆便举起铁锤,对准树杈上的铁铃铛用力敲起来——“当啷!当啷!”撞击声传开,整个山冲都是铁铃的声音,连角落弯里都躲不过。此刻,幼小的我仰望外婆,看她高举手臂、努力挥舞,只觉得地球引力拦不住她的高大。
后来长大了些,打点就成了外婆布置给我的作业。我日日按时完成,仿佛这已是一个孩子在他五岁时应做到的。我喜欢打点,每日屁颠屁颠、连跑带爬地来到后山坡,上气不接下气地望向铁铃铛,任凭它周身的斑斑锈迹散发透亮、清冷的味道,吸引我学着外婆的模样,两手握住铁锤,脸绷得如满弓的弦一般——咬紧牙!抿住嘴!踮起脚!举起,再举起——“咣!”被我用足了力气敲响的铃铛,震荡出层层声波,压弯了菜田,颤抖了山头,眩晕了鱼塘。而社员们会在声波减弱的关头,头顶草帽,神态自若地扛着锄头,从羊肠小路汇拢来,借铁铃的余音,把互相的招呼、说笑送遍这片山冲,好不热闹。
外婆自然都听着了。她夸我点打得响。我咯咯地回笑:“他们都听我指挥呢!”
个头再高些,母亲把我从外婆家接回来,送进“半边街”学堂。我这才知道“打点”的说法只存在于田间地头,学堂给它安了个学名,叫“打铃”。“半边街”的铃声是受着琅琅书声熏陶的,且日复一日,早已褪去了山间野气息。它浓缩成一个哨子的模样,挂在老师的脖子上,随着老师嘴里的吹气,发出一声声又尖又亮的鸣叫,短促响亮。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学生气的“打铃”。
再次见到,我已经读三年级了。铃铛掌握在一个留短发的女校长手里——懵懂得很,直到长塘小学,我才晓得学校原来还有校长的。这会儿的铃铛终于是个“铃”的模样。它比哨子大,却较铁铃小,刚好一个贴紧手掌。叮铃铃摇起来,响声且清且脆。校长有节奏地摇晃铃铛,边用方言大声催促:“上课哒!上课哒!”我好羡慕校长手里的那个铜铃铛,但直到离开“长塘”,我都没有摸过。
电铃风行的时候,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师毕业的我正在家乡的中心小学——我的母校“半边街”教书。当然,这会儿没有了铃铛,也已无了“半边街”。取而代之的是一幢高大的三层教学楼,紧邻操场。值班老师只需用手一按,铃声便陡然炸响耳边,在没有遮挡的操场上横冲直撞,唬得学生们前一秒还在玩闹,下一瞬便朝向教室,蜂拥而入。一时间,电铃似乎才是孩子王。
后来啊,电铃也老了。它卸下一身疲惫,同锈迹斑斑的铁块相伴。电铃窝在广播室的电脑里,铁块悬在香樟树的粗干上。有电时,值日生按下鼠标发言:“同学们,上课了。专心听讲,大胆发言,每天进步一点点。”停电时,值日生轻触铁块,些微的摇晃足够推动气流,瘦高的打铃人、孩子好奇的手指和那遥远时空里的童年一起,奏响叮铃铃的童话。
要是学校有个小小的博物馆,收藏铁铃、哨子、铜铃、电铃……该多好啊!可以在多少人的记忆里泛起涟漪啊。如今,铁铃不见,老屋消失,只剩发黄的老照片里似有铃声阵阵,在每个早晨,每次朝阳,每回默记起外婆的嘱咐时,唤回一个孩童,仰头、张望……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