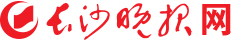淋漓笔墨 写意性情——专访花鸟画家苏高宇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兆红 实习生 张晓瞳
苏高宇是近年来颇受艺术界和收藏界关注的画家。出生于湖南湘西的他,已在北京闯荡20年,作为颇有影响的大写意花鸟画家、文艺评论家、作家,其绘画作品以水墨为基调,注重笔墨的书写性与文人画的精神内核,力求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大巧不雕、自然率性,被认为在当代中青年大写意花鸟画创作领域具有典范意义。
日前,长沙晚报记者在长沙专访苏高宇,听其畅谈中国画创作的内在理路及个中甘苦。
接通中国画传统文脉这条幽径
长沙晚报:您的画很有传统的文人气息,接通的是“由内而外”的中国画传统,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的中国画创作方式?
苏高宇:如果说我的画有传统的文人气息,它主要得益于读书。事实上中国过去的画家没有哪个只会画画的,至少也是文学家或者诗人、书法家,这是一个门槛。中国画就我个人来说,之所以这么喜欢,在于它文学上的魅力,它不是单纯的工匠活,中国画是需要内在修养的。
因为这样,我对这门艺术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为什么敬畏?你走进去之后才知道它的难度、它的高度。
拿明代晚期的徐文长来说,当时他是在戏曲创作上有名,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在戏曲创作上有极高的成就,他有自己的思想深度,他在书画上才达到了令人仰止的高度,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写意花鸟画鼻祖;还有郑板桥,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在那之余他才画画,画兰竹。可以说他的毛笔是思想火花的载体,是思想火花的一种总结。中国画的魅力就在这里。
我个人在探索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但这条路最终还是曲径通幽的,通什么呢?通到中国画传统文脉的这条幽径上来了。

名利心太重,很多事情没办法做
长沙晚报:刚才讲的是道与术的关系,绘画艺术的境界、格调,需要学问与阅历的滋养。那么,您追求的中国画最高境界是什么?
苏高宇:中国画过去有句话说得好,叫“少学老成”,它注重童子功,但也强调一定要达到相应的年龄才能达到相应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是笔底下的那种苍茫雄厚之后的平淡境界,更多的是人生阅历之所在。它需要的那种平淡不是平庸,不是寡味,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含蓄的、隐藏的艺术。中国画的“老成”需要这样一种境界。
比方说吴昌硕活了84岁,他达到那个境界基本上也是70岁之后了;然后是齐白石,徐悲鸿说过一句话,“如果齐先生在60岁走了的话,中国画坛就没有齐白石了。”至于黄宾虹,他活到90多岁,最后才呈现黑墨的画法,“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黄宾虹在70岁之前的画都非常干净,一点不像他最后10年画里的那种黑里透亮,隐藏着人生的哲理之光。这说明中国画确实太需要时间了。
现在我的心态放得非常缓。对我来说,只要有饭吃,没有人干涉我画画,没别的什么要求。现在好多人跟我说要求创新,说你传统功力那么深了,不要再钻研传统,我就说,一个人在散步时的姿态,不是他睡觉时的样子,我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漫步。漫步是什么?就是一种不断吸收、吐纳的过程。我不能一上来就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这样表面上你迎合了很多人的需求,之后你怎么办?要是名利心太重,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它是一个长跑项目。你不急躁,顺其自然,作品自然而然地就好,而且这种好没有人工气。
我现在不去横向比较,我的定位是纵向。我跟前辈们还有很大的距离。所谓最高境界不好说,因为年龄不同、阅历不同,结论会有变化。
湘西文化滋养出反其道而行的思维
长沙晚报:您从湘西走出来,湘西这方水土滋养了沈从文、黄永玉。湘西文化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苏高宇:我5岁开始涂鸦,天生喜欢画画。那时乡下是木板房,我用木炭在墙上画,父亲做工回来看着墙上的画生气,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因为是在木板上,父亲就用湿抹布很生气地擦掉,但第二天等他去上工了我又画,画完他回来又擦,周而复始。
我是土家族,那方山水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让我养成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思维。像现在画画之后的题词,很多时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头脑中自然而然出现奇妙的东西。很多人画荷花,会写“出淤泥而不染”,我有次不知道怎么就题了一句“脚下全是淤泥,到哪儿去不染”;还有一次我写了“花开在眼中,影子落在心里”,很多女性朋友看了很有感触。我觉得这种感触就来自湘西的文化土壤,是一种神秘潜在的力量。
同时,我在性情方面向往自由,画画时比较随性浪漫,这都与潇湘的这方水土有关系。

人物名片
苏高宇,土家族,1966年生于湘西。2010年获选文化部年度人物;2012年获新华网“年度最受藏界关注奖”。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美术》副主编、《中国画收藏文献》主编、《国画研究》杂志学术顾问。有散文集《恍惚》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要举报